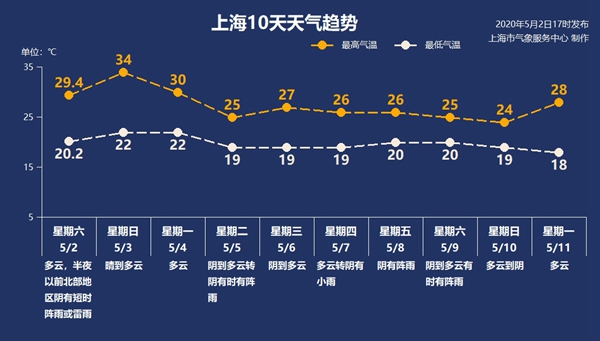对接世界,向更深层次开放迈进——写在上海自贸试验区10周年之际
记者 杜晨薇一 1999年11月10日,中国入世前夜,中美迎来了第25轮谈判。谈判持续了6天6夜,剩下最后7个问题仍无法达成共识。 美方代表团放出风声,...
记者 杜晨薇
一
1999年11月10日,中国入世前夜,中美迎来了第25轮谈判。谈判持续了6天6夜,剩下最后7个问题仍无法达成共识。
美方代表团放出风声,机票已经订好,他们准备打道回府。中方没有放弃,7个问题,3个同意,4个坚持立场,要求美方让步。
最后时刻,美方同意了意见,双方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这是中国开放史上的重要一笔。
2001年中国入世后,经济总量逐渐从世界第六位冲到第二位,服务贸易从世界第十一位上升到第二位,货物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更是跃居第一位。
然而,成为“世界工厂”之后,中国在全球定价和定制方面的话语能力仍单薄;国际投资规则体制从双边到多边,也有不少新变化需要调适。开放进程中的中国,持续面临新命题。
时间来到2013年。7月11日,中美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双方达成共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为基础进入实质性谈判。这在当时被视为重要的外交突破。
仅仅两个多月后,9月29日,作为对谈判成果的巩固和呼应,以负面清单为管理模式的中国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正式迈入建设进程。
中国此举向国际市场传递了鲜明信号:中国将在新的国际投资规则坐标系下,实践更高水平的开放。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就是中国更主动参与全球竞争、推进国际投资自由化谈判的齿轮。
今天,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即将走过10年,在新的全球政经格局下国际经贸规则正不断调整,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国再次面对“何以开放”的时代命题。
习近平总书记为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确定路径、指明方法,要求上海自贸试验区“加快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形成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使自由贸易试验区成为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
既往的实践经验也向世界郑重宣告:中国的开放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在全球化奔腾的浪潮中如此,在当下汹涌的逆流中,也不会改变。
二
9月6日,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后,商务部透露将推动出台全国版和自贸试验区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引发市场热议。
负面清单,一种国际通行的外商投资管理办法。简单来说,写在清单内的不能做,清单之外,“法无禁止皆可为”。
事实上,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后,就率先试点了负面清单制度,并在金融服务、跨境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等多领域、多层面进行实践。
2019年,“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成熟定型并正式写入《外商投资法》。“这是自贸试验区为国家全面开放做出的最大贡献之一。”浦东新区发展改革委体制改革处处长郑海鳌说。
然而,10年之前,当“负面清单”四个大字第一次出现在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建设总体方案中时,各界还颇有争议。“特别是围绕开放到何种程度、开放后能不能管得住等问题,方案经历了多次大修。”时任上海自贸区研究院秘书长陈波回忆。
实施负面清单管理,不是简单的“一纸禁令”,背后涉及系统性的体制改革和可能造成的产业链冲击。2013年我国第一张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出炉时,里面有18个门类,89个大类,419个中类,1069个小类,190条管理措施。不在其列的事项,就意味着必须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把项目的核准制改为备案制。
人们更担心,放宽外资进入的领域后,会对本土产业链形成挑战。这样的纠结,在中国入世前后也曾有过。“历史多次证明,中国开放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从来不是保护出来的。”陈波说。
三
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实施,使中国实现了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接轨。不过,清单需要逐步压缩、简化,才可能带来持续的开放效应。第一版负面清单发布后不久,政学两界纷纷呼吁给清单“瘦身”。
2020年,新出炉的负面清单明确“在全国范围内取消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外资股比限制”的当天,路博迈和贝莱德两家知名的资产管理公司就向中国监管部门提交了在中国设立外商独资公募基金公司的申请。截至今年2月,全国第一批外商独资公募基金已全部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开业。
中国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10年来完成7次“瘦身”,制造业条目清零,服务业准入放宽,条文数量从190条缩减到27条,业界称“仅次于美国,比日本还少”。
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主任朱芝松宣布,上海自贸试验区新设立的外资企业已经全部实行备案制,率先构建起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截至去年底,上海自贸试验区新设外资项目已超1.4万个,累计实到外资586亿美元,相当于每分钟就有逾1万美元实到外资“到账”。
四
2013年,发明出人类历史上第一台显微镜的德国企业蔡司,将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内的贸易公司,升级成为中国区管理总部。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实施自贸战略后,都嗅到了扩大开放的气息,纷纷强化在华布局、增加投资。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一年内,新增外商投资项目2015个,比上一年猛增近5倍。
不过,自贸试验区并不是政策洼地,更不是中国市场面向全球的“短期利好”。“通过自贸战略,我们不仅要解决外资落地的问题,更要通过制度集成创新,解决外资的持续经营问题。”华东政法大学教授、自贸区法律研究院院长贺小勇说。
比如货物贸易领域,开放后不仅要把货放进来,还要放得快、政策稳定,像进口水果这样的短保鲜产品才能在国内形成市场。通过首创一线“先进区、后报关”,二线“批次进出、集中申报”等措施,智利农场采摘的车厘子,48小时内能进中国的超市,整个口岸通关全面提速降费,无纸化率达到98%。
蔡司拓展了在华业务后,也碰到新问题。“客户要买一台价值几百万元的高端医疗设备,得飞到海外去看货。如果想在境内看,就得先完税。”蔡司中国首席运营官谢磊说。为解决海外高端商品的展示成本问题,上海自贸试验区推出“保税展示交易”政策,让高端设备不需完税即可在区内展示,甚至可以“出区”,带到国内一些专业展会上展示。
自贸战略历经10年改革深化,基本解决了企业“可不可为”的问题。不过,伴随开放程度逐步加深,整个开放系统中的短板问题也有所显现。要想让企业投资中国、看好中国,必须帮助企业从“可为”走向“有为”。
五
为了更好体现自贸战略的扩大开放效能,近年来,上海自贸试验区逐步将改革重心放在强化改革系统集成上来。创设本外币一体化运作的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发布境外职业资格证书认可清单和紧缺清单,上海逐渐成为全球资本、数据、技术、人才等流动性要素的配置节点。
去年,依托上海自贸试验区率先推出的“全球营运商计划(GOP)”,蔡司把原先放在香港的转手买卖业务转移到上海。2017年前后,蔡司在上海全年仅产生2000万元人民币离岸贸易交易额,到2022年已经突破了6亿元人民币。谢磊说,跨国公司过去将研发、生产放在上海,将金融功能放在香港或其他国家,是现实需要。“今天,立足上海就能合理配置各方资源,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离开中国,离开上海。”
9月1日,一台从瑞典空运进口的二手发动机经过再制造的工艺后,运往上海自贸试验区内的沃尔沃建筑设备(中国)有限公司。很快,它将在一台国内卡车身上实现“再上岗”。今年7月3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明确可以“在重点行业试点再制造产品进口”。
“出于业务可持续发展的考虑,我们第一时间向上海自贸试验区申请开展部分境外再制造产品进口业务,第一单业务如今已经落地。”沃尔沃服务与备件部副总裁陈朝平说。
在外界看来,上海自贸试验区再制造产品的进口放开,多少有一些姗姗来迟。在全球制造行业内,再制造的市场规模已经超过千亿美元。
不过,回顾自贸试验区建设10年,不难看到寓于其中深刻的理念变迁:中国的开放,是主动衔接国际高标准规则规制的开放;中国的开放,正在从过去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更深层次的制度型开放迈进。
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申卫华透露,目前上海还在加紧研究《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中的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边境后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型规定,为推动中国加入高标准经贸协定提供上海的实践支撑。
“这需要静下心来逐条研究国际经贸规则,并充分利用中央赋予浦东的地方立法职能,加快形成一批更有针对性的制度创新成果。”贺小勇说,“当然,挑战或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中国从入世那天起,就已经在对接国际经贸规则了。我们有实践,也有信心。”
一
1999年11月10日,中国入世前夜,中美迎来了第25轮谈判。谈判持续了6天6夜,剩下最后7个问题仍无法达成共识。
美方代表团放出风声,机票已经订好,他们准备打道回府。中方没有放弃,7个问题,3个同意,4个坚持立场,要求美方让步。
最后时刻,美方同意了意见,双方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这是中国开放史上的重要一笔。
2001年中国入世后,经济总量逐渐从世界第六位冲到第二位,服务贸易从世界第十一位上升到第二位,货物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更是跃居第一位。
然而,成为“世界工厂”之后,中国在全球定价和定制方面的话语能力仍单薄;国际投资规则体制从双边到多边,也有不少新变化需要调适。开放进程中的中国,持续面临新命题。
时间来到2013年。7月11日,中美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双方达成共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为基础进入实质性谈判。这在当时被视为重要的外交突破。
仅仅两个多月后,9月29日,作为对谈判成果的巩固和呼应,以负面清单为管理模式的中国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正式迈入建设进程。
中国此举向国际市场传递了鲜明信号:中国将在新的国际投资规则坐标系下,实践更高水平的开放。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就是中国更主动参与全球竞争、推进国际投资自由化谈判的齿轮。
今天,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即将走过10年,在新的全球政经格局下国际经贸规则正不断调整,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国再次面对“何以开放”的时代命题。
习近平总书记为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确定路径、指明方法,要求上海自贸试验区“加快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形成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使自由贸易试验区成为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
既往的实践经验也向世界郑重宣告:中国的开放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在全球化奔腾的浪潮中如此,在当下汹涌的逆流中,也不会改变。
二
9月6日,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后,商务部透露将推动出台全国版和自贸试验区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引发市场热议。
负面清单,一种国际通行的外商投资管理办法。简单来说,写在清单内的不能做,清单之外,“法无禁止皆可为”。
事实上,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后,就率先试点了负面清单制度,并在金融服务、跨境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等多领域、多层面进行实践。
2019年,“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成熟定型并正式写入《外商投资法》。“这是自贸试验区为国家全面开放做出的最大贡献之一。”浦东新区发展改革委体制改革处处长郑海鳌说。
然而,10年之前,当“负面清单”四个大字第一次出现在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建设总体方案中时,各界还颇有争议。“特别是围绕开放到何种程度、开放后能不能管得住等问题,方案经历了多次大修。”时任上海自贸区研究院秘书长陈波回忆。
实施负面清单管理,不是简单的“一纸禁令”,背后涉及系统性的体制改革和可能造成的产业链冲击。2013年我国第一张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出炉时,里面有18个门类,89个大类,419个中类,1069个小类,190条管理措施。不在其列的事项,就意味着必须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把项目的核准制改为备案制。
人们更担心,放宽外资进入的领域后,会对本土产业链形成挑战。这样的纠结,在中国入世前后也曾有过。“历史多次证明,中国开放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从来不是保护出来的。”陈波说。
三
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实施,使中国实现了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接轨。不过,清单需要逐步压缩、简化,才可能带来持续的开放效应。第一版负面清单发布后不久,政学两界纷纷呼吁给清单“瘦身”。
2020年,新出炉的负面清单明确“在全国范围内取消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外资股比限制”的当天,路博迈和贝莱德两家知名的资产管理公司就向中国监管部门提交了在中国设立外商独资公募基金公司的申请。截至今年2月,全国第一批外商独资公募基金已全部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开业。
中国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10年来完成7次“瘦身”,制造业条目清零,服务业准入放宽,条文数量从190条缩减到27条,业界称“仅次于美国,比日本还少”。
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主任朱芝松宣布,上海自贸试验区新设立的外资企业已经全部实行备案制,率先构建起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截至去年底,上海自贸试验区新设外资项目已超1.4万个,累计实到外资586亿美元,相当于每分钟就有逾1万美元实到外资“到账”。
四
2013年,发明出人类历史上第一台显微镜的德国企业蔡司,将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内的贸易公司,升级成为中国区管理总部。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实施自贸战略后,都嗅到了扩大开放的气息,纷纷强化在华布局、增加投资。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一年内,新增外商投资项目2015个,比上一年猛增近5倍。
不过,自贸试验区并不是政策洼地,更不是中国市场面向全球的“短期利好”。“通过自贸战略,我们不仅要解决外资落地的问题,更要通过制度集成创新,解决外资的持续经营问题。”华东政法大学教授、自贸区法律研究院院长贺小勇说。
比如货物贸易领域,开放后不仅要把货放进来,还要放得快、政策稳定,像进口水果这样的短保鲜产品才能在国内形成市场。通过首创一线“先进区、后报关”,二线“批次进出、集中申报”等措施,智利农场采摘的车厘子,48小时内能进中国的超市,整个口岸通关全面提速降费,无纸化率达到98%。
蔡司拓展了在华业务后,也碰到新问题。“客户要买一台价值几百万元的高端医疗设备,得飞到海外去看货。如果想在境内看,就得先完税。”蔡司中国首席运营官谢磊说。为解决海外高端商品的展示成本问题,上海自贸试验区推出“保税展示交易”政策,让高端设备不需完税即可在区内展示,甚至可以“出区”,带到国内一些专业展会上展示。
自贸战略历经10年改革深化,基本解决了企业“可不可为”的问题。不过,伴随开放程度逐步加深,整个开放系统中的短板问题也有所显现。要想让企业投资中国、看好中国,必须帮助企业从“可为”走向“有为”。
五
为了更好体现自贸战略的扩大开放效能,近年来,上海自贸试验区逐步将改革重心放在强化改革系统集成上来。创设本外币一体化运作的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发布境外职业资格证书认可清单和紧缺清单,上海逐渐成为全球资本、数据、技术、人才等流动性要素的配置节点。
去年,依托上海自贸试验区率先推出的“全球营运商计划(GOP)”,蔡司把原先放在香港的转手买卖业务转移到上海。2017年前后,蔡司在上海全年仅产生2000万元人民币离岸贸易交易额,到2022年已经突破了6亿元人民币。谢磊说,跨国公司过去将研发、生产放在上海,将金融功能放在香港或其他国家,是现实需要。“今天,立足上海就能合理配置各方资源,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离开中国,离开上海。”
9月1日,一台从瑞典空运进口的二手发动机经过再制造的工艺后,运往上海自贸试验区内的沃尔沃建筑设备(中国)有限公司。很快,它将在一台国内卡车身上实现“再上岗”。今年7月3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明确可以“在重点行业试点再制造产品进口”。
“出于业务可持续发展的考虑,我们第一时间向上海自贸试验区申请开展部分境外再制造产品进口业务,第一单业务如今已经落地。”沃尔沃服务与备件部副总裁陈朝平说。
在外界看来,上海自贸试验区再制造产品的进口放开,多少有一些姗姗来迟。在全球制造行业内,再制造的市场规模已经超过千亿美元。
不过,回顾自贸试验区建设10年,不难看到寓于其中深刻的理念变迁:中国的开放,是主动衔接国际高标准规则规制的开放;中国的开放,正在从过去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更深层次的制度型开放迈进。
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申卫华透露,目前上海还在加紧研究《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中的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边境后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型规定,为推动中国加入高标准经贸协定提供上海的实践支撑。
“这需要静下心来逐条研究国际经贸规则,并充分利用中央赋予浦东的地方立法职能,加快形成一批更有针对性的制度创新成果。”贺小勇说,“当然,挑战或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中国从入世那天起,就已经在对接国际经贸规则了。我们有实践,也有信心。”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