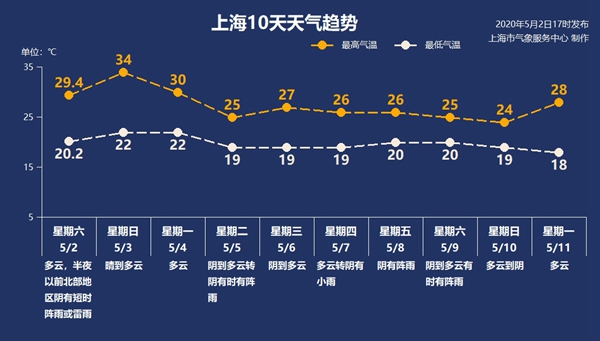复旦科技考古团队重现40余位无名烈士相貌
考古队员的发掘日记。黄海华 摄 记者 黄海华 无名烈士,是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一个“群像”。在复旦大学考古队的探寻下,40余位无...
考古队员的发掘日记。黄海华 摄
记者 黄海华
无名烈士,是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一个“群像”。在复旦大学考古队的探寻下,40余位无名烈士的相貌得以被世人知晓,这在国内尚属首次。其中一位还重获姓名——崔海治。
近日,一场无名烈士墓地分子考古研究成果展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志和堂启幕。在第十个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让我们一同走近崔海治以及众多无名烈士。
寻亲
高高的鼻梁,薄薄的嘴唇,细长的眼睛。通过颅面复原技术,崔海治烈士的相貌以数字化形式被生动呈现,他的侄儿崔玉岐看了大为惊叹:“实在是太像了!”他拿出了大伯的照片,兄弟俩不仅五官轮廓相像,就连眉宇间的神情也颇为相似。
这场科技探寻缘起于一场寻亲之旅。2019年10月,崔玉岐来到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南村寻找其三叔崔海治的墓地,他手里只有当年晋绥边区发放的烈士证明和晋绥野战军独立第二旅新兵营负责人王公太所写信件。无奈年代久远,难寻踪迹。
巍巍太行,吕梁苍苍。在革命战争年代,这里曾经“养兵十万牺牲一万”,刘胡兰等仁人志士就出自这里。吕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通过查阅史料、走访村民,发现南村埋葬着国际和平医院第七分院多名因抢救无效牺牲的烈士,崔海治极有可能就在其中。
今年2月,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文少卿课题组受邀对墓地进行发掘和鉴定。7月,经过DNA比对,确认了墓地中一位无名烈士正是崔海治。
密码
展览现场,目睹烈士遗物,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任重书院院长陈尚君“内心很不平静”。他说很自然想起了那首创作于抗战年代的歌曲——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正顽强地抗战不歇……“最让人伤感的是,南村烈士墓地出土的49具遗骸平均预期寿命仅为20.5岁,他们中很多都还是孩子。”
塑料牙刷、纽扣,子弹、步枪弹,展出的90余件器物,仿佛在无声诉说那段艰苦卓绝的日子。有的烈士身中数弹,有的做了截肢手术仍不幸离世,还有的年纪轻轻却因营养不良、工作强度过高而患有退行性关节疾病。
根据骸骨的碳、氮值变化,烈士们的个体生活史被还原。“他们在生命最后阶段摄入的很有可能是小米,‘小米加步枪’如此真实。”文少卿告诉记者。
回家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为让更多烈士“回家”,文少卿课题组在这条少有人走的路上坚持了8年。
2015年,首批中国远征军(缅甸密支那战役)将士的DNA鉴定失败,委托方想要送到英美权威机构测试。经过沟通,文少卿课题组获取了27具中国远征军遗骸,并成功鉴定其父系遗传类型,推测其可能的地理来源,为几十年来一直在寻亲的家庭带来希望。
此后至2018年间,课题组与田野考古学者合作收集了8个遗址的572具烈士遗骸,涉及滇西保卫战、长沙会战、平遥遭遇战、高台战役、淮海战役等。如今,课题组已完成国家英烈DNA数据库1期的建设。寻亲者上传自己的DNA数据后,系统会自动与英烈DNA进行比对。正是基于这一数据库,课题组确认了平遥遭遇战中牺牲的八路军某团原政委邹开
胜的遗骸,了却其时年73岁女儿的寻亲之愿。
震撼
现场考古勘探非一个“苦”字能形容。漫天的风沙和刺目的阳光,是当地常见的天气。墓地附近没有厕所,带去的水壶虽然灌得满满的,但大家没时间喝,也不敢喝。采访中,考古队员几乎闭口不提这些困难,他们说得最多的是触及心灵的震撼。
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博士后熊建雪告诉记者,“我在做年龄鉴定时,发现绝大多数烈士都比我以为的要小,很多只有十几岁,我就想到自己十几岁的时候在做什么,真的很心痛,更由衷地向他们致敬。”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